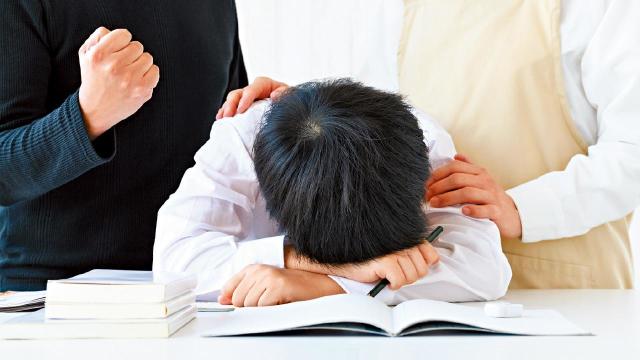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褚蓥
一、现实问题
近期报复社会型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多有发生,社会舆论一般将之归为偶发性、个体性事件,不少专家亦指出,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犯罪数量明显减少。这符合实际情况吗?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22年,九年间,我国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总数的确有了明显的下降。这说明我国社会的整体治安水平的确得到了较大改善。
同时,在这九年间,公安机关立案的杀人刑事案件也呈现快速下降趋势,从2014年的约1万起下降到2022年的约5千起,减少了近一半。这说明个体间的激情杀人、报复杀人等情况也在减少。
但同期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数据并不支持上述说法。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22年,我国人民法院审理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一审案件收案数保持长期增长的态势,从2014年的21万快速增长,直至翻倍。从长期来看,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并没有随着整体犯罪数量的减少而减少,反而呈现出逆势增长的态势。换言之,几乎所有类型的刑事案件数量都在下降,只有两类刑事案件数量在不断增长,即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两类犯罪,尤其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数量在总体犯罪案件数量中的占比不断提升,甚至逐渐成为主要犯罪类型。整体社会环境的改善并没有带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数量的减少。认为经济发展能够减少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尤其是报复社会型犯罪数量的高企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情况呢?
二、成因探析
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成因,学界曾有过总结。一般认为有如下成因:第一,个体成因。个体成因分为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所谓先天因素,即行为人本身所具有的人格障碍。所谓后天因素,则比较复杂,包括个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个体在社会交往中遭受挫折、个体丧失对社会的认同感等。
第二,舆论原因。网络媒体,尤其是自媒体对放大个体成因发挥了不可推卸的责任。人们可以相互攻讦、相互诋毁、随意批判,网络暴力、人肉搜索频频发生。同时,某些自媒体对关注者加大煽动,存心利用。这些情况都会激发行为者的情绪,容易引发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第三,社会原因。有学者借助默顿的“社会结构失范理论”提出一种解释,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结构简单,只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三个阶层,而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加速,人们在物质财富、权力以及社会关系方面占有的资源也出现了加速分化的情况,而对于这一变化,弱势群体并不能做出及时调适,于是滋生不满情绪,诱发报复社会的犯罪。这种情况,如果再加上社会阶层固化等原因,容易推高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的整体数量。
第四,示范原因。有学者指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尤其是报复社会型犯罪具有不良的示范效应。一旦某起案件爆发,具有相似动机的个体就容易受到诱导,产生相似行为。所以,媒体对这类案件的跟踪报道,尤其是对案件发生原因,比如社会因素方面的探讨,会对潜在的犯罪行为人带来引导和暗示,会使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悲惨境遇是社会导致的,从而降低个人罪责感,诱使他们实施报复社会行为。
这些归因的确能解释近期爆发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的部分根源。比如,@未明子、@章北海official等一大批自媒体网红的长期极端煽动,特别是对阶级对立情绪的反复煽动,的确对危害公共安全案件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在无锡“11·16案”中,这一因素的影响格外明显,是重要诱因之一。
但上述原因并不足以完全解释近期发生的案件,特别是珠海的“11·11案”。在“11·11案”中,司机樊某驾驶高级汽车冲撞他人。所以,樊某并不属于弱势群体,而是有车有房的成功人士。所以,就算前述各项因素全部成立,在社会原因方面,归因依旧是有缺失的。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常德“11·19案”中,以及此前发生的一系列危害公共安全案件中,比如2023年广东发生的温庆运驾驶宝马车冲撞行人案。所以,我们应重新审视这些案件的社会根源。
通过仔细比对这些案件,可以发现,这些案件有几个明显共同点:
第一,它们都是个体性犯罪,即单人的犯罪,而很少有两人及以上的犯罪。
第二,行为人不计后果。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通常并不考虑自己所要面临的处罚。他们普遍抱着自我毁灭的态度,即“大不了一死”的心态。
第三,行为人具备特定的环境条件。行为人之所以能够长期预谋,选择自认为效果最佳的报复社会的地点、方式,且不计后果,采用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实施犯罪,是因为他们有相应的环境条件。这一环境条件主要是行为人所处的伦理集合体破碎,甚至完全坍塌。
我国社会是一个家社会,即一个以“家”为基本形态的巨大的伦理集合体。而这一巨大的伦理集合体是由众多的小伦理体构成的。而在珠海“11·11案”、无锡“11·16案”,乃至广东“温庆运案”中,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到伦理体坍塌的情况。
首先,家庭生活缺失。珠海“11·11案”的行为人樊某刚经历一场离婚纠纷。无锡“11·16案”的行为人徐某金是一名独自在外读书的大学生。广东“温庆运案”的主犯温庆运的家庭生活很不幸,长期被父亲交给房东照顾,且犯罪前刚刚与父亲大吵一架。家庭生活缺失,导致了行为者伦理体最内圈基本空缺,乃至完全坍塌。
其次,属于外来人口。多起案件,比如无锡“11·16案”、广东“温庆运案”的行为人都是外地人,在本地并无根基。外地人的身份,导致行为人在本地缺少其他亲属,也未必有能够交心的朋友,这导致行为者伦理体中间圈坍塌。
最后,特定城市环境。这些案件大都发生在城市,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城市中,比如,珠海、无锡、广州等。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无法形成所谓的同乡之谊,而是彼此保持一种陌生人的关系,这导致行为者伦理体最外圈坍塌。
观察这些案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行为人的伦理体处于半坍塌甚至完全坍塌的状况。而伦理体坍塌,导致行为人一方面在遇到困境时,缺少有效的社会支持以帮助行为人疏解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供问题解决建议;另一方面更容易无所顾忌,无所牵挂,而做出极端行为。因此,伦理体坍塌,是导致此类报复社会型犯罪的一个重要精神根源。
导致伦理体坍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个人方面的原因,比如个人不善于处理家庭关系、个人主动离家就学等;也有家庭方面的原因,比如父母长期在外经商,无力照顾子女等;更有社会层面的原因,特别是城市化过程中,全社会关注经济发展,而忽视伦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对策建议
针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激增的问题,一般认为应该通过法治手段来加以解决。比如,新华社给出的解决方案:“要增强社会治理的‘刚性’,防范打击必须强之又强、硬之又硬。”
还有意见认为要做好犯罪预防,通过排查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纠纷的方法,来预防此类犯罪的出现,“要提升社会治理的‘柔性’,推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往心里走”。甚至还可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公共安全风险进行预测和预警,及时发现和处置潜在的安全隐患”。
但问题是,报复社会的犯罪行为人是不计后果的。既然犯罪行为人无惧惩罚,那么,用刚性的法律去治理此类犯罪行为人,便只能导致“法律失灵”的结果。所以,一味强调“刚性”手段,无法解决当前难题。
同时,对社会矛盾进行排查,的确能够减少此类犯罪行为。可是,社会矛盾始终存在,并不可能被彻底化解。我国政府一直很注重对基层的治理,采用了网格化管理、“互联网+”等模式与手段。但这些模式与手段并没有改变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数量不断增加的趋势。这说明,一味依赖所谓的“柔性”手段,也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治标不治本。
那么,应该采用什么措施来应对当前的难题呢?既然报复社会犯罪行为的重要社会根源之一在于伦理体的坍塌,那么我们就应该将重点放在恢复与增强伦理体上。具体而言:
第一,增强家庭伦理观念。近几十年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这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但我国对家庭伦理建设的投入明显不够,在学校教育、社会宣传、人才遴选等方面,都没有体现这一点。这导致我国民众出现漠视家庭伦理、轻视家庭关系的情况。
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扭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转变为经济建设与伦理建设并重。在这两者中,伦理建设是基础,决定了经济建设的高度,经济建设能动地配合伦理建设。这即是说,政府应从学校教育、社会宣传、人才遴选方面,多管齐下,重视家庭伦理建设。比如,政府要增强学校对学生的伦理教育,把家庭伦理作为学生的主干课之一,并对学生的行为操守进行考察;要加大社会宣传力度,深入挖掘好家风典型,提供好家教范例;注重对党员干部的家风要求,凡是提拔干部,必先考察家庭关系。
第二,构建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40多年的城市化,在发展我国经济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社会的样貌,撕碎了同乡、亲属、朋友等关系网。这使得我国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通常只能依靠自己,而无法从社会上找到有效的支持力量。而且,越是处在社会底层,就越是无法获得社会支持力量,也就越孤独、无助。
要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着力构建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所谓社会支持网络,是差序格局的中间圈与外圈。如前所述,差序格局的内圈为家人、中间圈为亲属与朋友、外圈为同乡等熟人以及社区服务机构等。社会支持网络建设的着眼点应放在亲属、朋友、熟人、社区服务机构上。
要做好这项工作,政府需要花力气培育熟人关系网络。人与人之间只有先熟络起来,才可能建立起所谓的熟人间的伦理关系。这种关系网络的建立,需要双方都敞开心扉,将对方纳入到自己的熟人圈中,将对方当做“自己人”。在这一方面,政府可以组织复兴传统文化、修建祠堂、开展传统文化宣传以及组织传统文化礼仪活动等。
同时,政府还应当积极培育符合这一方向的社区服务机构,为民众提供相应的文化服务与精神支持。
另外,这些社区服务机构也可以参考欧美国家的成功经验,设置“安全阀”机制,即提供情绪发泄室、情感倾吐室,以伙伴陪伴发泄、伙伴陪伴倾听的方式,帮助对方渡过难关。